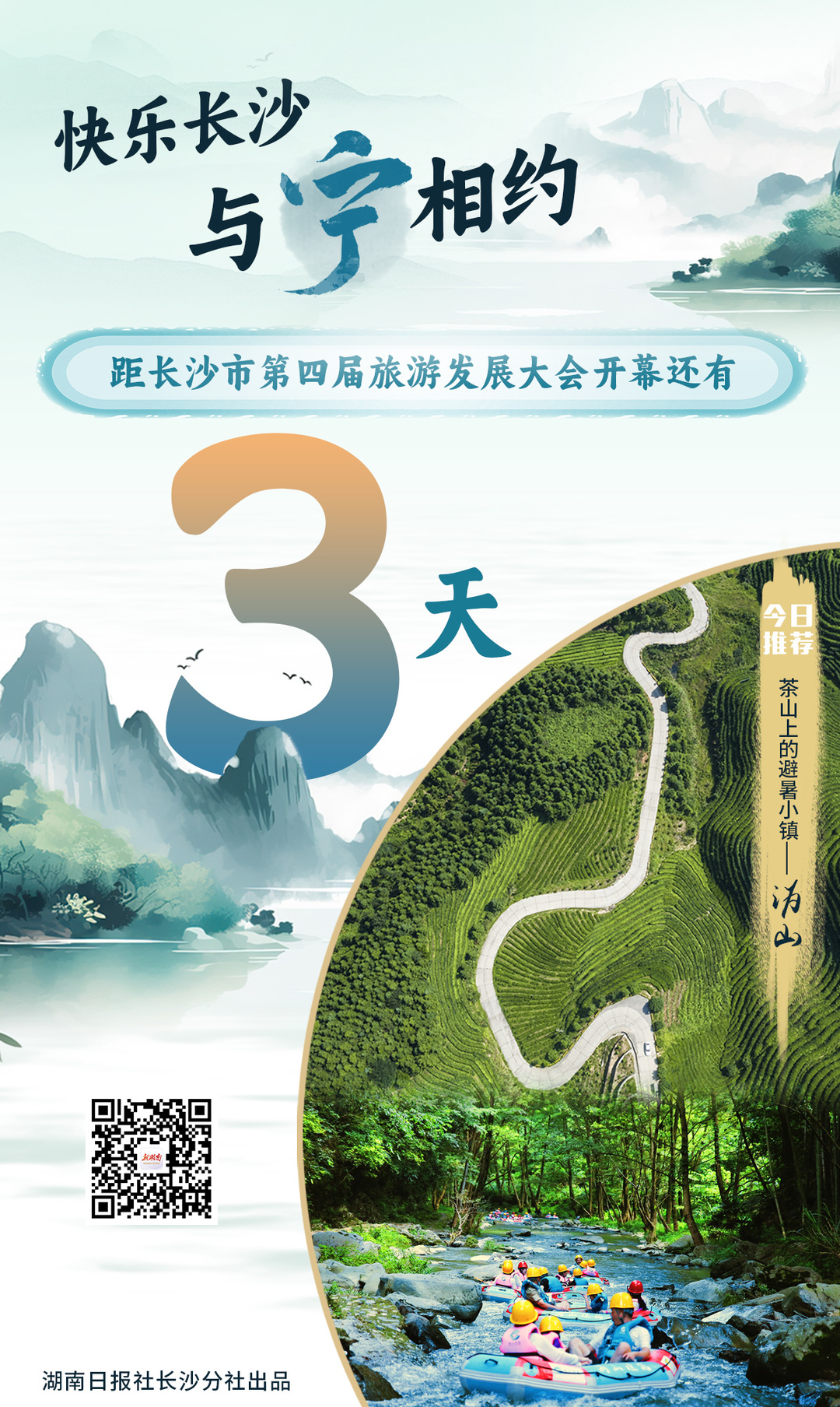
湖南日报·新湖南客户端记者 李曼斯
黄材水库旁,刀削斧刻的石壁间龙飞凤舞“沩山”两个大字,山脉自此起始。峰岭迂回折返,你躲我藏,如神龙盘踞,见首不见尾。
再行10余里,高山从身侧拉远,视线逐渐开朗。沩山三十六景宛如长卷入画,一一扑入眼帘。
我得以一见那千年奇树“猫公刺”。不禁失笑,这哪里是树,分明是鸟喙往池塘啄水,连带那山体也成了旱鸭身躯,跟着活泼起来。

走到近处,它的形象陡然高大。伞盖下的枝干盘根错节,遮天蔽日,只余细碎光柱零星洒下。其高约5米,伸手远不可及。灌木竟高大如乔木,实为罕见,应是长了1200年的功劳。
相传此树为“四枝灵官”树,有惊邪附体,招惹不得,人人敬而远之。直至和尚塔的僧人们念了七七四十九卷经书,使其吸天地之灵气,吮塔陵之惊魂,消其邪气,庇护众生。自此愈发枝繁叶茂,成了“佛祖灵树”,供人参拜。
不知晓人沾染了几分福气,反倒是一旁的枫树,因缘巧合得到桃蜜子树的青睐,互搂腰肢,生死相托,被戏称为“枫桃联姻树”,与“猫公刺”一起声名远播。
行至高氏宗祠,偶遇一场檐下听雨。
雨滴从青瓦滑落,断断续续,奏出曲调。老戏楼上,恍惚间有花影随之轻摇,身姿绰约,想必只是绮念罢了。

对那些雕梁画栋而言,这不是绮念,而是一场略微久远的沉寂。高氏族谱上记载:“民国十一年,长沙同和班曾来此连续唱戏16天”。沩山深处,16天的花腔婉转,16天的满座惊欢,这是何等盛况!
时至今日,岁月侵蚀朱漆,却来不及将斑驳记忆掩埋。戏楼两侧,刻有清光绪四年(1878年)至民国时期长沙同和班、清盛班、南楚武麟班等戏剧班在此演出的《二进宫》《长坂坡》《弘庵寺》等7个戏曲名单,各戏班名称甚至演员的姓名均有详细记载。先人的艺术光辉变得鲜活清晰。
将历史的云烟抛于身后,赴一场山水之约。
沩山架起一座琴骨,任飞流直落成弦,碎成珠玉敲击卵石,清脆动人,煞是好听。好乐者禁不住诱惑,跋山涉水也要一观。
山路越行越窄,两百米外,只能踏石越溪。好在溪水清澈喜人,兰花抚得衣角湿润,胸腔里腾起一种说不清的雀跃。

声响已全然在耳前了。“瀑布自高而下,前挂晶莹,倾流到渊,作大朵昙花散落,溅雪飞霆,声撼林谷。”清代学者陶汝鼐如此描画芦花瀑布,亲眼看来,竟只字不差。
要看懂沩山,不得不登顶九折仑。
九折龙腾,一跃将沩山分割成地形迥异的南北两大片。峰岭以北,莽莽崇山;岭南则豁然开朗,一望几十里田畴陇亩如川。
从沩山入巷子口,往往途经此地。匆匆一眼,俯瞰山河,也能看得心潮澎湃,豪情万丈。
山顶有奇石霹雳,名为“镜子石”,光白可鉴,雨后莹镜如玉,亦为奇观。
虽无春日梯田采茶,亦无夏日凉意扑面,秋日沩山仍令人为之动容,因其巍峨、因其厚重、因其绵长。
责编:封豪
一审:封豪
二审:王晗
三审:刘永涛
来源:湖南日报·新湖南客户端

版权作品,未经授权严禁转载。湖湘情怀,党媒立场,登录华声在线官网www.voc.com.cn或“新湖南”客户端,领先一步获取权威资讯。转载须注明来源、原标题、著作者名,不得变更核心内容。



 关于我们
关于我们 湘公网安备 43010502000374号
湘公网安备 43010502000374号